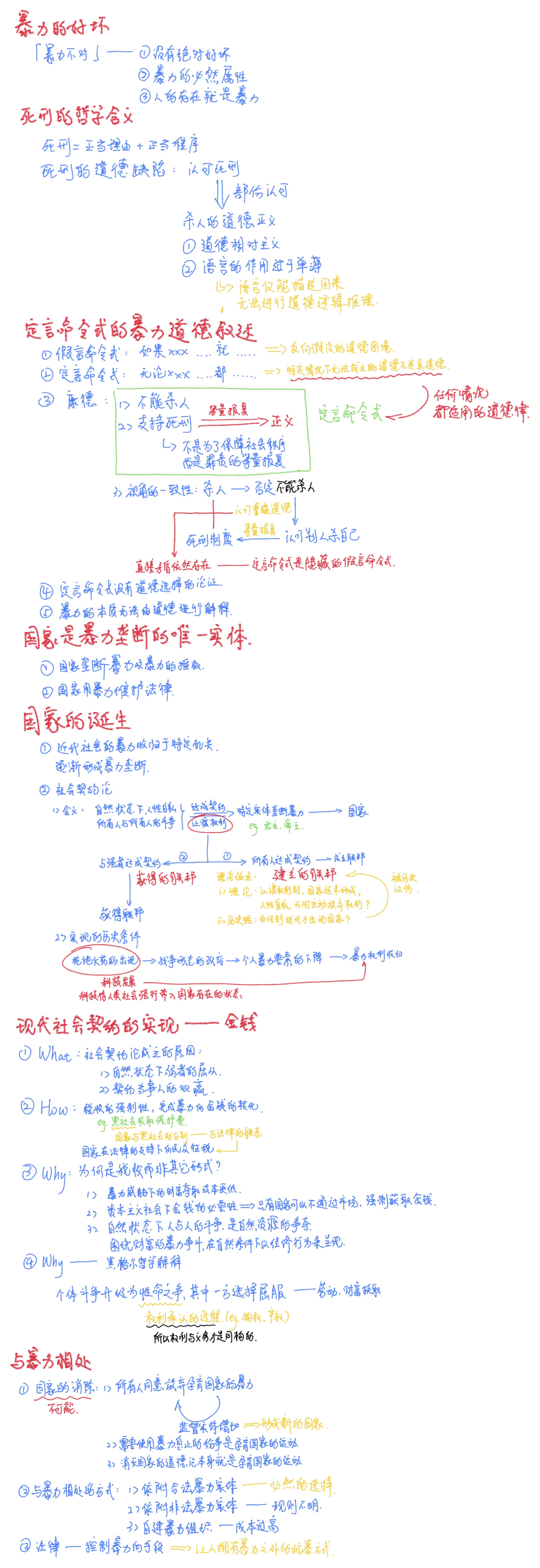
第9页
人人都说暴力不好,为什么又会为它着迷?为什么又要崇尚暴力呢?真是奇怪。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那便是:我们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第12页
最原始的权力,就是以暴力为前提,令对方服从。暴力便是这样,不由分说地令对方服从,从而产生权力。当然,前提是要比对方强大,遭遇对方抵抗时,也具备将其压制到底的实力。只要能做到这些,就能以暴力获得权力。权力也是暴力的成果之一。
可以这样说,无论是食物、安全,还是权力,只要还有什么东西是不用暴力就得不到的,暴力就不会从我们的世界消失。于是,现实情况变成:暴力与我们形影相随、若即若离。所以,我们活着就是一种暴力。
第17页
如果仅因为犯下凶案这一条理由,就同意将人处死,那就变成谁都可以用任何手段杀死凶犯。受害人的家属也可以抓住犯人,对他行刑。还有,既然依托于法律的死刑是被允许的,那么是否只要依托于法律,政府就可以将任何人处以死刑呢?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此可以看出,只有“正当的理由”和“正当的程序”二者同时存在时,死刑才会为人们接受。
尽管如此,依然无法改变执行死刑就是杀人的本质。肯定死刑的人,在理由和程序上将死刑和普通的杀人区分开来,实质上也只是将杀人以好或不好来区分。因此杀人通常而言是不对的,却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绝不可以。只要理由和程序正当,在某种情况下杀人也无妨,即不否定所有的杀人行径。于是,在杀人这一终极暴力面前,我们依然要考虑它好坏与否。对于暴力,我们很难持彻底的中立态度。永远无法与暴力彻底划清界限,这或许就是人性的可悲之处。
可是这样一来,“杀人不对”这一道德标准就无法严密自洽。肯定死刑,就意味着认同在某种情况下杀人也无妨。当然,反对死刑,就意味着“绝不能杀人”这一道德标准占了上风。可是,既然多数人赞成死刑,“不能杀人”在社会中也就无法站稳脚跟——否则,大多数人就不会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杀人也无妨了。
第22页
“没人有权剥夺别人的未来”“每条生命都是无可取代的,没有谁能抹杀他人的存在”——这些也都是不能杀人的理由。但仔细思考,这些理由不过是换个说法把“不能杀人”重申一次。杀人就意味着“剥夺别人的未来”,也是“抹杀唯一的存在”。这些回答只是用其他说法表述“不能杀人”,并不能解释为何不能杀人。
“被杀死的人不能重生”的说法也是一样,“杀人”本就相当于“让对方不能重生”。
第23页
换言之,不能杀人不是根深蒂固的道德法则。乍看上去,这一准则似乎根本不需要理由,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完备的理由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既然如此,也就难怪许多人会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杀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一定这样想:“原则上来说不能杀人,但既然没有一个确凿的理由,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就可以像执行死刑那样将人杀掉。”
第24页
话语无法赋予道德绝对的正义性
或许有人会因为找不到不能杀人的根本原因而不满,认为一定有某种绝对的理由能够支撑道德的正义,否则岂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杀人了? 可是,找不到绝对理由支持的,不是只有“不能杀人”这一项道德要求。其实任何道理都一样,因为话语的性质就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话语仍无法赋予道德绝对的正义性。发生了A,形成了B;A和B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一话语很适合用来记录或描述这些情形,却无法从根本上证明“为什么不能做A(或为什么应该做A)”。 就像我们试图从道德角度阐述“不能杀人是因为会有人伤心”时,立刻就会产生“为什么不能让人伤心(如果是为了让人伤心而杀人不就行了吗)”之类的反面论调。当我们继续对其反驳,则又会出现新的反对意见,如此循环不息。这就是所谓的无限递归。 因此,从话语的性质来看,不存在可以证明“不能杀人”这一道德正确性的理由。话语的性质只能说明“如果你杀了人,就会被捕,接受处罚”之类法律上规定的因果关系。
第26页
话语的无力
那么,话语是否对扶正道德毫无帮助呢? 也不能这么说。话语无法说明特定的道德根据,却可以说服人们接受某种道德。 用刚才的例子来说,“有人会伤心”无法从根本上说明“不能杀人”这一道德标准,却可以从“杀人后会有人伤心”这一因果关系上来描述事实。 “杀人会有人伤心”,只看这句描述,确实仅仅表达了“A导致B发生”这一因果关系。然而,同时也向对方传递了“因为杀了人会有人伤心,所以不能杀人”这一讯息。虽然只是记述事实,却有让听者接受某种行为规范的力量。这被称为话语的“述行性力量”。 也就是说,通过记述事物之间的关系,话语能够传递一定的道德信息,说服对方采取某种行为。正因为话语有这样的力量,才不能把它和道德分割开。尽管话语无法证明道德的绝对正确性,人们还是停止不了说教。就算无法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不能杀人,但从话语性质上来看,只要对方能接受“不能杀人是对的”就行了。
第34页
人们给道德寻找根据的行为,反而制约了道德。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能杀人时,我们便不由得中了圈套,很容易陷入必须找出一个理由作答的尴尬境地,担心若不这样做,“不能杀人”的道德原则会由此崩坏。可是,扶正道德的举动并不一定总能让它更加坚固,反而可能使其在特定条件或假说的限制下变得更加脆弱。看似维护道德的行为,实则是一种对道德的弱化。这便是道德的逆命题。
康德以定言命令式思考道德,是为了将道德从各类条件或制约中解放出来。定言命令式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无条件成立的道德律,换句话说,康德眼中真正的道德,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做依据的。特定情况下无法成立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康德对定言命令式下的定义,就包含这一条。
第50页
因为谁都不能忽视,人是活在暴力当中的,无论你是否情愿。
前面强调过,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只能用暴力解决的事。生活中,我们也在不停判断某些特定的暴力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至少是“无奈的”),甚至和康德一样,终日思考为了实现正义是否必须杀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深信不能行使暴力。当然,也有人认为“无论什么场合,暴力都是不好的”。可只要缜密地思考一番就会明白,这样的想法毫无意义。假想一位女性将要被人强奸,她身边恰好有一块大石头,于是用石头打了对方的头,逃出险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站在“一切暴力都不好”的立场上,反对她用石头打对方的行为吗?显然不能。如果反对,就相当于让她乖乖被侵犯,从本质上默认了加诸她身上的暴力。
也就是说,“任何情况下暴力都不好”这一看似恪守道德标准的观点和其表象相反,不过是眼看着暴力发生,却毫不反抗的“胆小鬼观点”,它反而肯定了暴力。这里我要再次重申,“任何情况下暴力都不好”看似在道义上很风光,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却是完全错误的。即使在道德立场上否认我们活在暴力中的事实,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不能直视这一点,就不可能批判真正的暴力(当然也不是让各位像康德那样赞成死刑。该赞成怎样的暴力、反对怎样的暴力,与眼下的问题无关)。只要我们还活在暴力中,就无法不用好坏来区分暴力的性质,对其做出价值判断。将暴力分为好的和坏的,会为我们分辨敌人和战友提供帮助。
政治世界就是这样诞生的。
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中指出,敌人和战友的区别才是政治固有的指标。这里的“政治”指的是国家等政治概念,或权力行使、法律制定与战争等政治行为,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政治”或“行为主体”“行为”。这些政治主体组成世界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区分敌人与战友的过程。施密特认为,区分敌人与战友的过程暗含着一种对立,最终可能引发两方相互残杀。他所说的敌人与战友,是以能否对对方行使暴力为基准来区分的。划分敌友的过程,产生了国家等政治主体。
不得不用好或坏来区分暴力,说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必然的政治世界里。对我们来说,暴力究竟是什么呢?要理清这个问题,不能一直埋头于道德这片海洋中,还需要跨越到政治领域中去。
第57页
假设警察要抓一名罪犯。如果罪犯企图逃跑或反抗,警方就会使用暴力抓捕他。如果“暴力”这个词太重,也可以说以“物理实力”来抓捕他。总之要采取一种方式压制对方的攻击或抵抗,用更强的力量令对方屈从。如果罪犯的攻击或抵抗比警方的力量更大,警察就抓不住他了。所以警方必须做好准备,能够随时对罪犯行使比其攻击更强大的暴力。
同时,为了避免个人或其他组织拥有比警方更强大的力量,警察平时必须监视社会,取缔收缴暴力武器。正是这些与暴力息息相关的活动,才使国家拥有平息犯罪的力量。平息犯罪就意味着平息违反法律的行为,维护法律。换句话说,国家以暴力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诉诸武力镇压”,来维护法律。
对一个国家来说,它需要妥善组织警方活动,预备好力量,以行使社会中最强大的物理实力。如果没有储备,一个国家就无法治理犯罪,进而无法维系法律,最终无法统治社会。所以说,国家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诞生的。
第66页
为什么国家能够成为“赋予暴力权利”的根源呢?因为只有国家才具备物理实力,能真正取缔社会中产生的暴力。社会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暴力,只有国家有实力取缔这些暴力,确定它们之中哪些是违法的,哪些又是合法的、属于正当防卫。而我们就算认为某种暴力违法,只要它还没被取缔,就会存在于社会,暴力行使主体就依然能够在国家掌控范围之外行使暴力。所以,唯有以暴制暴,才切实支撑着国家——支撑着“赋予暴力权利”的根源。
第67页
暴力合法与否由国家来区分;其实这不仅仅针对暴力,国家对任何行为都是如此,用“这样还可以,那样就不行”的论调来区分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由此确立人们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
判断其他行为是否合法,与确立“赋予暴力权利”的方式相同。国家用实力取缔它认定“违法”的行为,在社会上确立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区别。用实力划分合法或违法这一本质始终不变。在我们看来,假若超越了国家认可的“合法行为”的界限,国家就会立刻发动被判定为合法的暴力,逮捕、处罚我们,实际上就是由国家活动划定人们行事的权利范围。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不过,这里的“权利”可不仅限于人权之类的东西,它泛指一切被法律承认的行为的可能性。
第68页
国家是一场运动。它不断确立或判断哪些行为在法律界限内,哪些行为在法律界限外;同时以暴力(行使物理实力)取缔超越法律界限的行为,从而设定社会中的权利关系(得到法律承认的行为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我们就看清了国家的本质。国家的一部分重要职能,便是进行一场暴力运动。这项运动划定了人的权利——告诉我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国家的定义——国家是一场持许存在的运动——垄断暴力,解释暴力,维护暴力垄断的运动。
第77页
社会契约论的出发点认为人类原本是自私的,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或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自然状态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推演而来的。
但社会契约论认为,人与人达成契约时抛弃了人的本性,对人类的“善意”怀抱期待。这是社会契约论的巨大矛盾,也是它的弱点。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弱点
第77页
社会契约论还有一项致命弱点,它无法说明国家为什么临到近代才形成。
换言之,在历史的长河中,社会契约论一直无法说明在社会中扩散的暴力权利为何直到近代才被统合在一个机关下。
如果像社会契约论解释的那样,人们能够依照契约自发地形成国家,那人类社会诞生之后,国家怎么会一直都没出现呢?实际上,直到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才第一次诞生了垄断暴力权利的国家。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性弱点
第85页
近世身份制度不是与近代对立的古旧遗风,它为统治阶级独占暴力权利做了准备。也就是说,尽管丰臣秀吉的刀狩令在方方面面都不完备,但它是近代国家形成迈出的最有效一步。
刀狩令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让百姓无法与统治权力对抗,而是一方面制约着人们原有的暴力权利,一方面试图将这一权利逐渐收于统治阶层的掌控之下。刀狩令并不完全限制百姓的拥刀权,但有效限制了使用暴力私了冲突的可能,并通过身份政治区分武士和百姓的暴力使用,收归暴力权利。
第87页
通过百姓自愿放弃的方式实现政府“合法独占暴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统一天下的秀吉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是用军事力量强迫百姓放弃暴力权利。
简单地说,丰臣秀吉首先组织起足够打败其他大名和民众的绝对强势的武装力量,用它确立自己在一大片领地的统一支配权。这种压倒性的力量对比迫使人们交出手中的暴力权利,由丰臣秀吉的武装力量垄断支配。
前面讨论社会契约论的时候指出,让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主动放弃暴力权利是不可能的。历史也证明确实如此。要让人们放弃一直拥有的暴力权利,需以绝对强势的武装力量为前提。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性弱点,被历史事实证伪。暴力的收归,是由更强的暴力支撑的。
第91页
为何在丰臣秀吉的时代能够诞生一个让大部分地区的人都交出暴力权利的强大军事组织?
这个问题很难解答。其实,社会契约论无法解释这类历史问题。
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论点很有启示意义。埃利亚斯指出,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成与枪支火药的发达程度是分不开的(参照《文明的进程》《宫廷社会)。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枪支火药的进步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军事形态。截至十六世纪,欧洲的战争都以军事贵族身披铠甲、骑马作战的重骑兵部队为战斗的主力军。这一军事形态要求每一位贵族战士具备很高的自主性。可以说,尽管是骑兵部队,贵族战士们跨上战马时的个人发挥仍是战斗成败的重要因素。那时的军事贵族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没有战事时可以自由回到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力空间。可以说他们归附于国王之下,但依靠自己的实力基础构建独立的权力空间团结作战。这便是当时国与国的战争方式。贵族战士之间如果发生矛盾,产生的武力纷争属于私战,是完全正当的。
可随着枪支火药的进步,军事贵族逐渐失去独立自主的能力。因为操控火药的步兵组成的集团战逐渐成为战争的主要方式。骑术精湛的骑兵在战场上一对一打败几个敌人的场面已经消失,他们在操纵火药的步兵部队面前几乎无力回天。这时,军事活动的主体从个人转移到了集团。
就这样,军事贵族愈发依赖或从属于统帅步兵部队的国王的权力。国王渐渐有了主动统帅兵力的能力,并开始限制以军事贵族为首的各阶层想方设法保有的暴力权利。
在考虑日本暴力垄断的形成时,欧洲国家的情况能带来很多启示。丰臣秀吉能够平定日本九州至东北的动乱一统天下,与他接手织田信长打下的军事基础密不可分。1543年,织田信长在军队中积极引入种子岛传来的火绳枪,从而大大改变了日本的军事状况。这一变化是颁布刀狩令的一大历史前提。秀吉通过刀狩令限制暴力权利,区分武士与百姓的身份,为近代国家垄断暴力打下基础。而使这一系列军事变化成为可能的,正是火绳枪的传人。枪炮火药的出现,降低了个人暴力要素的重要程度,这其实也是暴力收归的一种形式,暴力因为枪炮火药的出现,逐渐被收归到特定实体(即君主帝王)身上,成为垄断的暴力权利。
第101页
即使是受到恐惧威胁迫不得已定下的契约,只要在自然状态下成立,双方就必须遵从。其违法与否,是在有了国家之后依照国家内部的法律判定的。在国家从自然状态下诞生之前,它都不会是违法行为。
国家从自然状态下诞生的最原始契约必然是强制性契约。当然在国家出现之后,这类契约便会被判定为违法,由国家来消灭。可是,强制性契约恰恰对国家根基的稳固发挥着作用。这样的契约被国家认为是违法的,可同时又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说起来,这也算是一种矛盾。可只有这一矛盾能够判定各类暴力是否违法,因此也只得认为消灭暴力的暴力是合法的。这不过是矛盾的表现方式罢了。所以,纵然强制性契约是国家的基础,却不必感到悲伤,更不必贬低它。
第118页
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上暴力权利的唯一源泉,是因为国家握有能够制伏社会中其他任何暴力的物理力量,并宣称那些暴力是违法的。由暴力来制伏另一种暴力的运动,将暴力分成合法与违法两种。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能发挥制伏其他暴力、并将暴力按照法律区分开来的强大力量时,它才能将自己的强制力归为合法一列。
为什么只有国家才能强制征收民众的钱财呢?
第119页
用暴力夺取人们的劳动成果,比主动付出体力劳动或做买卖挣钱方便得多。而且,这样做能让依靠暴力运动存在的组织专心于暴力运动或权力工作,让它们更加稳固。现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钱,国家就无法运作任何活动。因此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弄到钱。相比之下,国家付出体力劳动或做生意,一定没有动用暴力从人们手中收取钱财、再将自己举办的活动归属于暴力或权力范围内更有效率。想一想也不足为奇,黑社会就是欣赏这种高效,才用暴力使自己寄生于民众的经济活动之中。
为什么国家要通过自认为合法的暴力向人们征收钱财?
第125页
只有当战争目的是为了让对方承认某一事物属于自己的时候,才能将其称为“承认之战”。这场战斗同时也是让双方承认谁更强大、谁对谁拥有支配权的战斗。战胜的一方会迫使对方承认“我如此强大,所以要支配你,并有权征收你的劳动成果”。这也足够说明赌上性命的战斗是一场“承认之战”。可以说,这场战斗就是让对方承认自己的强大,承认自己对事物的主权、支配对方和征收对方劳动成果等一切的权利。换句话说,这场争战确立了社会上最基本的权利。
黑格尔哲学中对暴力和权利的解释
第127页
黑格尔论述的重点在于,所谓“权利”,不是直接成立的。只有当以暴力为背景的社会承认它时,它才算成立。权利与暴力的实践以及人们对暴力的承认是分不开的。
这也是权利与义务同构的原因
第129页
黑格尔用“赌上性命的战斗”理论将霍布斯“出于恐惧订立的契约”概念精细化了。也就是说,通过“有关承认的战斗”,确立了各种各样的权利。用社会契约论分析,这一进程指的就是原始契约使得国家从自然状态中应运而生。
社会契约论将这不断完善的进程称作“契约”,这本身就是一种法律学上的表现方式。黑格尔则将其称为“权利的承认”,从更深层面剖析何为法律。当有人企图从权利范围中逃脱时,以法律为名的暴力就会发动,打击超越法律范围的行为——这便是法律的特征。“以法律为名发动暴力”是区别道德等其他规范与法律的方式。而只有国家,才能确定人们可以行使怎样的权利,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脱离了法律的制约,并发动暴力打压脱离法律的行为。因此,国家不仅是社会上暴力权利的源泉,也是各种权利的源泉。换句话说,国家拥有确定并承认社会各类权利的权利。正是这围绕着权利的权利,造就了国家的本质。
第136页
若暴力已经使支配关系确立下来,又能够征取钱财,就只能用另一种暴力阻止它了。无论怎样游说对方暴力不好,只要对方动用了,我们还是无法抵抗。最终,只有另一种暴力才能制止暴力。也就是说,为了阻止国家成立,就必须有能够监视、取缔、抑制它的暴力机构。换言之,为了不让国家成立,就要建造另外的国家。
第140页
“应当消灭国家”这一想法出于对国家的批判:国家建立在暴力之上,以暴力为基础压榨民众,滥用权力。这些批评本身没有问题,甚至还是有必要的。但若是将这种批判思维转化为道德标准,认为国家是坏的,应当消灭,批判思维就变了味道,自己的道德标准就成了绝对的正确。如此一来,任何反对的呼声都成了道德上的“恶”,成为不惜一切也要打倒的东西。为了支持不容许建立国家的“道德善意”,人们可以做一切强制性的事情。最终,消灭国家的运动,将会孕育出更压制民众、更暴力的国家。
消灭国家的道德论本身就是认可绝对暴力和建立国家的过程
第143页
只要回到“国家是什么”的问题上,就能很好地理解一部分国家为何解体,一部分国家为何尚未形成。
国家是社会暴力权利的唯一源泉。也就是说,它是切实要求垄断社会合法暴力的组织。有了这一认识就不难明白,之所以有的国家解体,有的国家尚未成立,都是因为合法的暴力垄断尚未形成,也就是政府的力量薄弱;或者历史上的暴力垄断机制还没有发生作用,人们依自己的判断自由行使暴力。
第146页
国家确实以暴力让民众服从,有时甚至可能镇压民众。但没有国家,只是没有了合法的暴力垄断,暴力本身绝不会从社会中消失。
所以,无论有没有国家,我们都必须用某种方式应对暴力。
第151页
国家其实就是一种暴力体制,其内容就是通过社会上唯一合法行使暴力的组织以暴制暴。它不依据人们各自的判断随意发动,而是有原则地禁止人们行使暴力,依据社会中唯一受到法律承认的组织做出的法律判断制裁其他暴力。
因此,一般来说,国家还是遵循以暴制暴的公式;但它试图通过法律的调控予以制约——这就给人们提供了用不同于暴力的方法抵抗暴力的可能。所以说,国家的存在使人们能够用不同于“以暴制暴”的方式,制约压制其他暴力的暴力本身。法律的存在,让人拥有以暴制暴之外的抗暴方式
以上摘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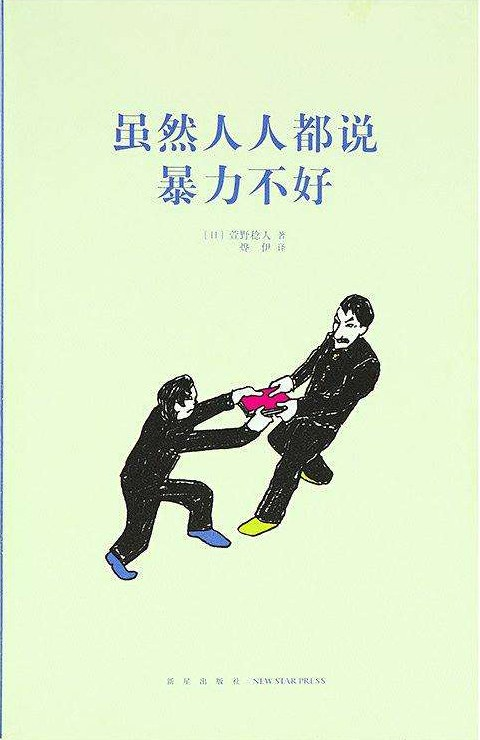
《虽然人人都说暴力不好》
作者: [日]萱野稔人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原作名: 暴力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誰もがいうけれど
译者: 烨伊
ISBN: 978751332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