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
对摄影评论并不是热衷,不过在这本饭泽耕太郎《写真的思考:摄影的存在意义》里,作者传达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审美角度——有的摄影作品是“以偶然的方式处理偶然,并将其必然化”。这里所说的偶然,毫无疑问指的是摄影行为本身的偶然,而所谓的必然,其实是摄影行为在凝结为摄影作品后,呈现给观众的必然。将「偶然」作为摄影行为的动机,是刻意扰乱意识性的控制、主动地选取错乱的过程。这在摄影创作中并不少见,但我们往往习以为常,而忽略了它作为摄影动机的深刻内涵。
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模糊定义,看似并没有给摄影艺术的解构来带多大困难,虽然难以从时间维度描摹摄影现代主义的全貌,但并不难从各种作品的共性中找到蛛丝马迹。作者在这部分提到了「断裂」与「再现」的概念。具体来讲,将客体从远观到近观的局部摄影,将客体从语言层面的所指转向能指的超现实主义摄影,都是一种以「断裂」为形式的创作,而摄影冲印技术的发展,又无不是「再现」的同义反复。现代主义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褪色,用作者的话来说,「尽管“后现代”这件衣服迅速穿上之后又被脱下,“现代”仍渗透在我们的骨头中、侵蚀着人类的思考与感受」。
从书名出发,「写真」一词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给它的定义——特指人物肖像的摄影类型。恰恰相反,写真的定义是具体而又宽泛的。在摄影技术刚刚进入日本时,人们对这样全新的成像技术抱有极大的好奇,什么是真实?如何描摹真实?这两个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尺度上陪伴着人类的绘画艺术,而摄影技术的出现,从根本上实现了写实主义,说到底,这恰恰就是一种对真实的写照,也是就作者想要表达的「写真」之意。摄影技术刚刚兴起的时期,也正是祛魅与复魅发展的时期,例如一些摄影师寻找非职业的摆拍者在棚内进行场景再现,利用摄影的写实主义特点进行的创作,不仅满足了受众对「写真」的心理需要,也让写真一词的定义更加深刻,这正是技术祛魅的实证。随着摄影印刷的普及,明信片的大量生产使耗费手工且价格昂贵的写真艺术快速衰退,新的技术浮上水面,为人类社会重新复魅。
摄影作为记录,或者作为创作的特性自然无需多言,更多的或许只是摄影艺术本身如何从这二者中进行选择的问题。不过,「死者的照片」却远远突破了这个论点,表现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内涵——死者不愿被遗忘,或者说生者不愿遗忘死者的羁绊。在现代社会以前,能够通过绘画艺术将自己的样貌「不朽」的,毕竟只是权贵等少数人。摄影术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这个原本只有少数人拥有的「不被遗忘权」。生者与死者通过影像的记录,获得了精神上的接触和联结,而死者真正的死亡,也被长久地延续到了被所有后人遗忘的时间点。遗照的拍摄角度、遗照的保留方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巨大差异,那又是另外的话题了。死亡作为人类无法回避的哲学命题,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通过摄影技术的大众化,传递到了普罗大众的生活中。
读书笔记
第 21 页
即使是美丽花朵、可爱小猫、美味料理等照片,如果以婴儿般未开化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的话,应该仍可窥见各种各样神话性的现象,如漩涡一般翻转着。持续端详之下,照片中的含意将会分支,多层化、流动性地变换和组织,最终产生出意想不到的结合。换句话说,初看普通的照片在深入审视后也有可能完全变为夸张而怪诞的异物。此外,还可能引发出逆转现象,将理所当然的东西转变为特异且独一无二之物,或者将特别的事物变成具有普遍性的东西。
第 32 页
十九世纪中叶,摄影技术在世界各地扩展时,曾经被视为一种具有魔力的装置:“被拍照时,灵魂会被抽取而出”。不仅在日本类似这样的流言全世界都在流传,换句话说,也就是会被引领去往死亡的世界。而十九世纪最被人喜爱的摄影领域之一,便是拍摄眼睛所不能见到的灵魂存在的灵异照片,这种喜好的理由多少也包含了摄影会抽取出灵魂的想法。
从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后,这样的魔幻性质却随着时代进步而急速消逝。因为器材与底片的进步,大众化的摄影转变为社会沟通的手段,成为仅是正确再现、传达图像的工具。而二十世纪末正式展开的数码摄影,更让我们确认了此一演变方向。时至今日,相机已经成为一种可以控制、容易上手、便于使用的工具。
第 42 页
拍摄这件事情既是“射击=杀死”,也是被“击中=复活”。
第 57 页
“全体”的解体
让我们暂且先以“断裂”这个名词来表达现代主义摄影的基本原理之一。就如斯蒂格里茨的《乔治亚·欧姬芙》所展现的,即正是这种断裂的典型。贯穿现代摄影的,便是从预先依照秩序安排好的“全体”中取出“断裂”的部分[或从中分离出某些片断],给观看者类似强迫症般的提示,这样的提示可将部分全体化。与眺望构图宽广的画面相反,这样一来反而会带给人一种奇妙的、切实的执著感。
以“特写”来说,这种在现代摄影中频繁出现的技法,是最容易让大家理解的例子。整个现代主义时期大量出现从脸、人体、建筑物、机械类、植物等全体中撷取一部分放大拍摄的题材,亦即全体的部分化,同时也是部分的全体化。这些特征超越了摄影师出身的国籍、经历、个性等,让我们体验到同时代性的感受。
这些摄影师使用特写技法所要追求的,就是将被摄体从日常视觉感受的全体性切割出来,并将其还原到单纯“物”的层面。
第 60 页
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语言当作能指[significant,符号的表征]与所指[signifie,符号的内容]的结合来处理,再各自对应到语言的“概念”与“意义”。根据他的说法,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随意的,不需要任何内在的动机或根据,亦即将能指与所指切割开来,让另一个语词“意味的内容”整个更换过去也完全可行。而类似这样能指与所指的再构成,于影像符号上执行比在语言符号上更加彻底,这是因为影像本身并不像语言一般有着严密的符码对应关系,相对来说能指与所指的连接也比较松散。
超现实主义者便利用摄影这种表现媒体,将原本影像上的意义作用因“间隔化”更加扩大。曼·雷或勃法所拍摄“一点都不奇怪”的帽子、汤匙、洋伞、街角景致等,不仅是剥夺了它们现实性的能指,还外加“情色性象征的书写”与其他所指结合。
第 66 页
再现与复制,使得影像生产力大增。借由摄影师之手,影像由日常脉络中被切割开来、赋予特别的意义,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再度被日常化、陈腐化。位于时代“尖端”的影像在短时间内不断地被消费,进而变得司空见惯且理所当然。为了对抗这种影像消费的空转,现代主义者们只能被迫不断穿上新衣,又不得不迅速地脱掉舍弃。
在历史上,没有其他时期像现代主义时代一般,不停开发各式各样新技法,反复进行技术性实验。而这个时期的摄影师们也必须自发性地频繁改变作品风格,此现象在其他时期也是很罕见的。也因为如此,从现代主义出现以来,“新奇度”便成为评价的绝对基准。
第 88 页
对艺术活动而言,让当时摄影师觉得感动且互享的那种欢愉,应该是对被描绘的、被拍摄出来的、与原物品完全一致的那种纯粹与惊奇。但将其推到极端来说,影像究竟是什么,对他们而言并不构成任何问题。与原物品几乎一致但却非原物品,这种类似制作出某种拟造物,有如机械机关一般的复制机制,才是他们深感魅力的所在。这让他们愿意沉迷其中,也是让他们努力于摄影与西洋画的原动力。
那是一种在没有任何干涉与关联下产生出的空虚,也是一种缺乏对象物的“写实”。正是这种状态,才让摄影师的作品展现出奇妙的真实感。
在这样的论点上,他们从事的并非是“艺术家”的工作,而是一种视觉上的娱乐,更接近新奇事物的展示。
第 96 页
一百六十多年前,摄影传入日本之际,适逢维系近三百年的江户幕府崩坏,新社会、新文化的框架重新形塑的时期。或许这种动荡不安、持续有重大变化的社会状况,也正好唤醒人们对“真实”的追求意识。此外,这个时期也正是摄影原有的魔幻性、神话性的思考,仍在摄影师与画家们间共通、共有,并以各种形式满地开花的时期。如前所述,明治中后期以后,当日本逐渐转型为现代国家的时期,摄影与绘画一体化的魅力表现,便急速地瓦解。
第 103 页
在达盖尔与塔尔博特发明摄影的时代,背后推动与支持他们的文化背景,其实正是该年代对“静物”的欲望与需求。
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前半期,支配欧洲人“观看”意识的“如画风格”美学,前文所描述的静物摄影也可以说是反映这种美学的一种产物。如画风格的美学意识后来也影响到十九世纪末形成的“画意摄影”,这部分已经于前文提及在摄影师们努力把照片“艺术化”作为目标的时代,如画风格的绘画便是他们的规范。也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符咒催生了摄影术,并成为摄影以惊人速度发展的契机之一。
简单地说,“如画风格”是将眼前宽广的世界以“边框”围起,当作一幅图画来观赏的意识。如果将这种意识彻底化,就会产生比起现实世界,图画反而让人更感到真实的倒错感。例如高山宏在《目中的剧场》中,描述了流行于十八世纪,一种称为“克劳德镜”[Claude Glass]的奇妙光学器具。这种“直径约四英寸的凸透镜”,可以选择观看者喜好的色调箔片,而透过这个工具观看风景时,可以变换、映照出对现实的凝视,就如同当时深受大众喜好的克劳德·洛兰[Claud Lorrain]的风景画一般。携带着克劳德镜的旅行者,只要将风景框进透镜,便能够随心所欲地享受“如画风格”的美景。以这种方式观赏风景的时代,也代表着观看者的行为“在结构上是和自然相对”的。
在某种意义上,如画风格也是将世界所有可能的影像都缩小,封存入“眼中”的一种意识。诚如多数评论者指出,在摄影术快速发展的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它将视觉从听觉或触觉等其他感官中独立出来并放大。“观看”与“拥有”被直接联系在一起,以“观看者”为中心,将世界再组织的欲望便从此昂扬前进。
第 109 页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0年代,不知为何,无生命的拍摄对象又再度复苏,成为摄影的被摄体。
……
这些静物摄影,与上一个世纪受如画风格美学影响而创作的作品有着微妙的差异。举例来说,如画风格美学意识中最重要的,便是以观看者为中心,“如人们想看的一般去看,如想切取一般的去切取”出画面并封存于取景框之中,以及审慎细致地去进行画面配置。但是1920至1930年代以物件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占据主角位置的不再是人类,而是对象本身。对象脱离人的控制而主张自我的存在,可在画面中任意、任性地繁殖,仿佛彼此秘密交谈一般。这种奇妙的氛围是我们观看这些作品时所能察觉到的,所以在这些创作中占据世界中心位置的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对象。
像这样的逆转,起因应该是将全欧洲逼迫至极限状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对过往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进行反思所产生的危机感。人们过去认为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确实而明确的,但在世界大战中,这种想法无可抑制地崩坏。因为异物化的巨大战争机器,让人们的生命无论在何处都暴露在致命的危险之下。这些应该受支配的物品,从人类的桎梏中逃脱并任意地到处漫游,让人觉得它们仿佛正在各处自我增殖。对象不再是能被操作的道具或工具,反之是活生生显露出敌意的异物。
不仅如此,1920至1930年代也是人们眼前陆陆续续、不断出现过往未曾看过之异物的年代。汽车、飞机、地下铁等新的交通工具,钢筋、水泥与玻璃所建造的充满设计感的建筑,泛着黑色光泽与钢铁肌理的机械在撕裂大地的同时又将空间多层次地连接起来,这些机械时代的产物,伴随着对几何学结构美的礼赞,但人们也意识到这些异物已经超越人类的控制范围,成为无法控制 的存在。而摄影师们面对这些不熟悉的物品,内心的憧憬与嫌恶、恍惚与不安、留恋与抵抗等思绪必然产生激烈冲撞。
第 120 页
就结果来说,摄影师们憧憬着超越人类思考与感觉尺度的物件本身它们所含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以及抱持着能够将其自由操作转化为任何变异影像的欲望,将这些冲动与摄影这个包含了各种矛盾的媒体结合,便形成了上述的静物摄影历程,并让摄影出现在既不是物件也不是影像[反之也可以说既是物件也是影像]的中间性区域。因此,摄影所拍摄下来的物件,一方面保存了物件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保持着物件作为影像可被操弄的矛盾。
静物摄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截取了摄影神话性、魔幻性思考中最直接的形式。物件与影像的双重性,既互相分裂也相互需要,对于此矛盾性的存在,只要人们还想去追求、厘清这种狂野的谜团,沉迷于静物的摄影师们的历史就会延续下去,不会断绝。
第 134 页
三浦雅士在他那充满启发与刺激性的摄影集《幻影般的另一人 现代艺术笔记》[冬树社出版,1982年]中提及,摄影师们虽然身处某处,却同时不具有身处该地的存在意识,也就是将自己定位在“幻影般的另一人”。他们的存在,就像是在不知不觉中混入玩耍的小孩里,计算人数时不管怎么数都会多出一个人来的妖怪——座敷童子。摄影师们“不管在什么状况下都不能够成为相关的当事者。他们经常是从情境中多出来、如幻影般的另外一个人,而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不是”。正因为如此,与摄影师们同处于封闭空间中的裸体女性,才能够平心静气地展现身体。而在战场或事故现场中,摄影师们也会自情境中抽脱,如此才能够以自在的,有时候甚至是旁若无人的方式,来进行拍摄。
这种专属于摄影师们的特权地位,便是由纯粹的“观看者”而来。当手中握有魔法般的装置,他们也同时可以将所有人事物转换成“被观看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摄影师的凝视已经转化成能扫视一切,绝对的神之视线,能在制高点上看穿所有人们、风景,以及处于其间的复杂脉络。但即便是具备如此全能视线的摄影师,也有一处是他们所观看不到的,那便是这些摄影师自身。
第 190 页
直到创造性的快照出现为止,摄影师与被摄体的关系,大致上不是保持远距,就是拉近距离。“家庭快照摄影”的拍摄者与被拍摄者间的关系,不用多加说明也知道是极端亲近的,而这种物理性、情感性的亲密度,便会唤起观看者无法压抑的怀念感受,或者是对逝去过往的唏嘘。反之,人类学者去未开化的部落拍摄,或者纪录悲惨的事故之时,就会与被摄体保持距离,因为他们需要一定的客观性,如果不这么做而投入自己的感情,恐怕就会漏失掉重要的画面。
所以,要如何判断作品是否为优秀快照的秘诀,便在于是否能够尽力保持不远也不近,以不断调整、接近及拉开与被摄体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却意外的相当困难。如果与被摄体产生亲近与习惯的感觉,就容易染上主观的色彩,进而卷入说明式的脉络中,最后容易变成刻板印象式的量产作品。反之,如果与被摄体保持相当的距离而致力于调整整体构图,并过度专注于按下快门的时机的话,被摄体又会变成不过是画面构成的素材而已。
第 244 页
“主题演讲”中,东松对自己的摄影方法做出如下表述:
摄影可说是科技中的媒体先驱,而摄影的特征,或者是百分之一秒,或者是十分之一秒,总而言之便是一种瞬间的静止。如果换种说法,也可以说摄影具备了杀死时间的机能。当然将无时无刻不在前进的时间止于一瞬的说法,其实也不过是停住了时间的影子而已。所以,似乎可以说摄影是虚构的,也确实是如此。它切割出一片生命的瞬间,将其置换到被称为照片的平面上,进行永久性保存。如果这世上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以实体存在的,那么,对拍摄黑白照片的人来说,他们就是使用黑白色调将彩色的世界抽象化,然后再进行永久保存。
这里他所说的将现实世界的时间切割之后再重新组合,其实是非常优秀的“现代主义”摄影观。把流逝的时间以几分之一秒为单位进行切割,并“将其置换到被称为照片的平面上”然后加以保存。这个切割与保存的程序,东松用“杀死时间”这样卓越的比喻来表达。也可以说,时间应该是处于假死状态,并由观看者的“手”加以“解冻”,让“被杀死的时间经由观看者再度苏醒”。
第 263 页
葬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记忆的祭典。这是一个唤醒来参加典礼的凭吊者们的记忆,让他们每个人都想起往生者在世的模样,而且是每个人都积极参与的魔法仪式。在这个白热化的心灵能量交换场所,摄影的“重生记忆”的力量也被最大限度地激活,即便对像我这种与父亲有点疏离的人来说[话说回来也并没有特意要疏远],看着他生前的姿态慢慢被播放出来,也无法遏抑强烈的哀痛与思念。所以,如果是容易被影响的性格,而且与逝者有着更加深刻联系的人,那就更加容易陷入狂乱的情绪里,这也是可以充分理解的。
在葬礼这种稍微脱出常轨而带有使人情绪激动的空间中,摄影与死者被刻意混合。某种意义上葬礼的主角,反而不是躺在覆盖着花朵的棺木中那位真正的死者[虽然这是有点奇怪的说法],而是祭坛上摆放的遗照。吊唁者凝视着往生者的照片,对着它双手合十祈求冥福,有时对着它呼喊,有时对着它流泪,看着它无法遏制自己情感的人更不在少数。不过这魔法的持续性并不长,当葬礼结束之后,这幅放大的遗照就会被收藏妥当,谁也不会再回头去看它。或许会被暂时放在厅堂挂着,但最终照片还是会被收到某处,或者被秘密处理掉。
人们有时也会将亡者的小照片与牌位一起供奉在佛坛上,但即便如此也会逐渐蒙尘,变成一年一次或两次的仪式性膜拜而已。记忆逐渐稀薄,认识逝者的人,也如梳子的梳齿逐渐脱落一般,一个随着一个消逝,遗照的魔幻性力量也会随之涣散,最后完全还原到只是一幅普通的照片而已。当对持有逝者记忆的人一个也不存在,所有人都将之遗忘掉时,也就是逝者初次成为完全的亡者的时刻。如果不是在艺术或文学上留下作品,也非在政界或商界活跃而留下昭彰恶名者,普通默默无闻的死者,大多都会走上如此的命运。
第 272 页
沿着这些照片回溯,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对一般的美国人而言,这些“死者的纪念照片”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即使他们是以今日我们无法理解的热情去持有死者的肖像,但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由于伴随着这样的持有,使他们也对生命更加坚持。伯恩斯针对当时的情况,在摄影集的序文中写道:
绘画是富裕的名人为了记忆而使用的媒体,该功能从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而摄影不仅能创造出视觉图像,同时也是能提供给所有人观看的媒介。因此,过往只有富裕阶层才能拥有的不死性,在摄影出现后便为千万人敞开大门。死者的纪念照片,不仅只是单纯唤醒记忆,例如年纪幼小还没拍过照片即过世的人们,纪念照片也可以替他们保持形貌。
第 272 页
让伯恩斯特别关心的,是美国与欧洲“死者的纪念照片”在本质上的不同。观看《睡美人Ⅱ》中刊载的拿破仑三世[E.阿贝尔特拍摄]、维克多·雨果[Victor-Marie Hugo][纳达尔拍摄]、疯王路德维希[LudwingⅡde BAVIERE][F.华纳拍摄]等人在床上过世的照片,即可以理解这些作品都遵从传统图像学,在拍摄时都强调堂堂正正的父性元素。在欧洲,不限于这些君主或者名人,在一般的死者的纪念照片中,对“王权、贵族制度、财力等特权于公开场合表明”的突出表现也很多。
与此相对,在美国就以“个性的丧失感与私人性的表现”为中心。大多数的场合,并不会作夸饰社会地位的演出。此外,美国的死者的纪念照片比较多都是收入盒中或以个人可以带着走的形式放置,而欧洲则会装上画框挂于墙上。美国的死者的纪念照片,较欧洲的酝酿出更多的亲密氛围,可以说是作为“日常生活中极其自然的一部分”来发挥其功能。
这样的差异,当然是由美国与欧洲传统文化的差异所衍生出来的。欧洲的家族比较容易保有国家、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的羁绊,与这种状况相对,身为移民国家的居民,美国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不得不以家族为单位,所以他们对死者也是家族成员之一的意识,希望能够继续这样保持下去的愿望,比欧洲家族来得更加强烈。而这样的愿望,均会加强想要持有死者的纪念照片的欲望。
他们“为了表明希望借由摄影的魔法来延长与死者的关系,而[在拍摄照片时]与时间立下契约”。
以上摘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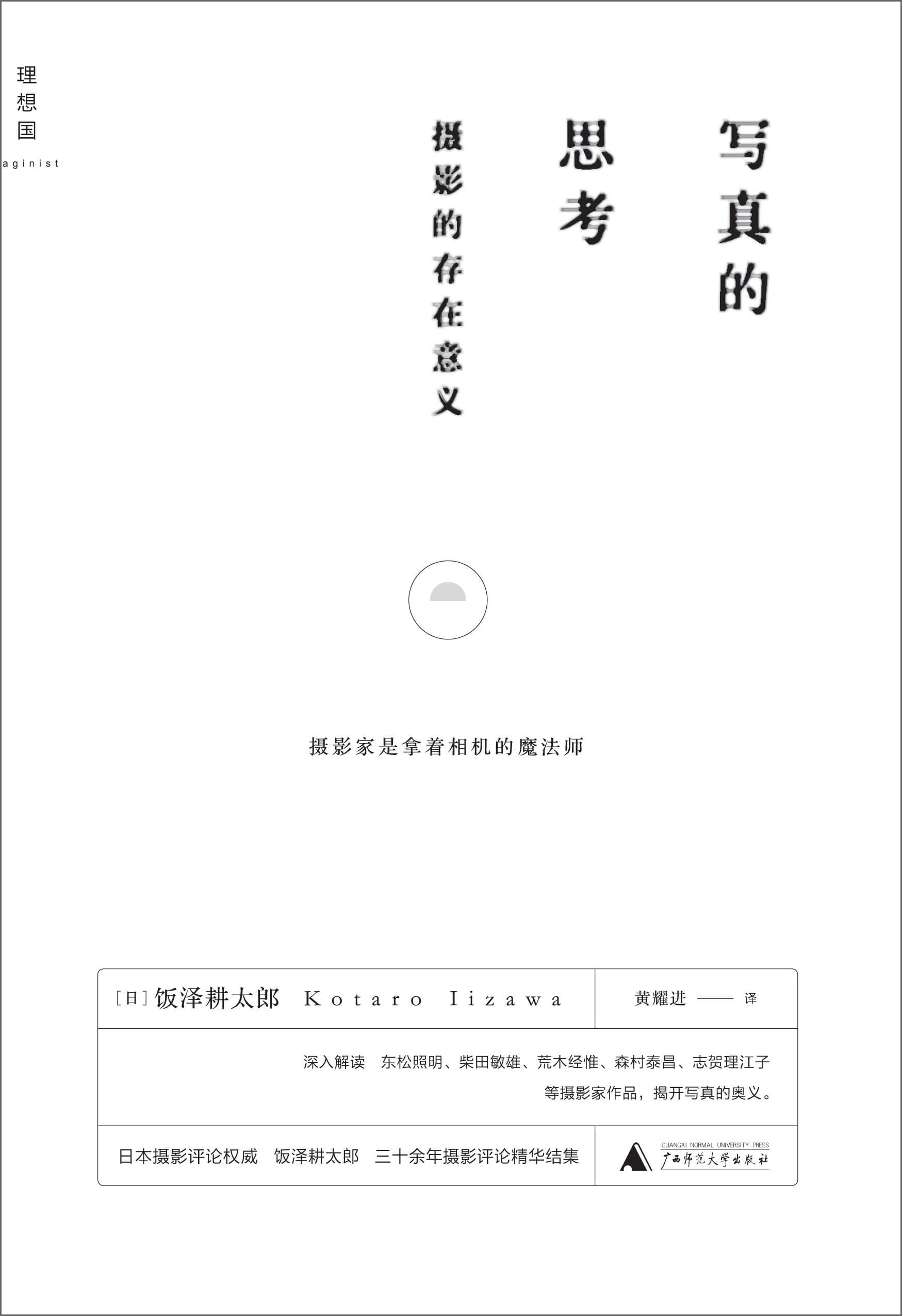
《写真的思考》
副标题: 摄影的存在意义
作者: [日]饭泽耕太郎
译者: 黄耀进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49562756